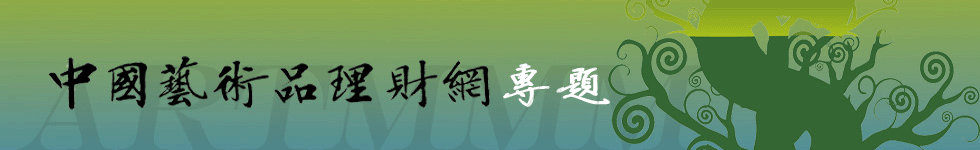无负苍生 吴冠中:丹青魂魄在 风骨冠中华
吴冠中偏爱的《双燕》(墨彩)

表现北京门头沟小山村的《桃花季节》(油彩)
一位出生在江苏宜兴的瘦骨嶙峋的老者,对中国油画和国画皆有筚路蓝缕之功,他自言崇拜骨头最硬的中国现代文化先驱、启蒙思想家鲁迅,而他本人一生的作为与言说亦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学贯中西,赤子怀抱,画笔常吟故园情;特立独行,大家风范,文心追慕民族魂。
在画家吴冠中谢世一周之际,让我们以人物版的一篇长文来对他表示祭奠。任何赞誉之词面对经历过社会生活的深重苦难和付出过艺术创造之苦功的人来说,都会显得黯然失色。那就只让一代艺术大师的思想和足迹来自我印证。或许我们应该留意,吴冠中成就了什么?是什么成就了吴冠中?他一生的追求启示何在?
我们的社会需要各个领域的俊杰与英才,可人们却较为吝惜一个“英雄”的称谓,更鲜有文化、艺术界的人物被冠以“英雄”的名号。或许因为艺术的创作常常是艺术家自己关在斗室里完成,就像直到90岁高龄还笔墨伺候的吴老先生那样,人们对他们的“英勇行为”难窥究竟。
让我们来为一直在为他的祖国、故乡、亲人与同胞画像的人也画一幅素描吧,如果我的文字能具有一种生动、鲜活的表现力。或者,我们该拿出城市中的一小块空间,用那剖面可以自然呈现水墨山水画的大理石立一尊雕像,永久地纪念和追忆那曾经用一支画笔荣耀过他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令世界惊艳的人。
怎一个“苦”字了得
1919年是中国苦雨腥风的年份。
吴冠中是在贫寒农家降生的一个苦孩子,笔名“荼”,即苦菜之意。
他住在宜兴闸口北渠村几间矮小的祖屋里,小时候常在离家不远的一片野草地——坟场上玩耍。母亲生了六个孩子,体弱多病,繁重家务全由做小学教员的父亲打理。家中仅有的十几亩田地养活一大家人,父母拿出平时积攒的血汗钱供子女上学。小冠中懂得其中滋味,甚为发奋,每次考试都争取班里或学校的头名。
人家曾对他父亲夸赞:“茅草窝里要出笋了。”
18岁,刚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书一年,就遭逢日本侵略军攻占卢沟桥的“七七事变”。
国难当头,他随师生颠沛流离,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木头房里上课,到过湘西的沅陵,又辗转贵州的贵阳,再到云南的昆明,直至落脚四川的山城重庆。
“因交通是大问题,学校没有办法做到集体行动,只能给学生发放路费,由学生自己想办法。从昆明一路连绵到重庆,我细心观察荒村、废墟、贫穷连着贫穷的大地,真是一条苦难的长城。我苦难的祖国,还抚育着我们这一代苦难的子孙。”
苦难家庭的孩子常怀苦心,苦难国度的学子善于苦读。
在杭州艺专的7年时间,受到留法的校长林风眠、教授吴大羽、蔡威廉、方干民、李超士、雷圭元、刘开渠等影响,吴冠中得益于注重个性解放的开放式教学方式,同时在素描基础训练、法文课语言训练两方面大有长进。而绘画系的课程包括油画和国画,二者兼学,为他日后对油彩、墨彩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像老师们那样去法国留学——勤工俭学,成为不少学生的梦想。吴冠中把攻读法语作为实现梦想的准备。对于学油画的学生来说,“拼命也要学好法语”,正像一个学歌剧的学生,一定要学会意大利语一样。
在重庆大学担任建筑系美术课的助教时,他用业余时间去中央大学旁听法语课,并到“文化中心”沙坪坝的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包括小说原文和中译本,边查字典边阅读,半小时翻一页也要“啃”。机遇,就是这样“等”来的。
1946年,全国遴选公派留学生考试举行。
27岁,好不容易考上去法国留学的政府公费留学生,却要面临和新婚妻子朱碧琴的4年别离。那时万里之遥,拮据的小两口付不起探亲的路费,而通信又是一种令人焦灼的漫长期待。
在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吴冠中师从四五十年代名震巴黎的重要画家、苏费尔皮教授,受益匪浅。“他观察对象强调感受,像饿虎扑食,并将艺术分为两路:小路艺术娱人,大路艺术撼人。”教授还把美和漂亮区分开来:美,是触及内在和灵魂的艺术感觉;而漂亮则更多的是作用于感官的体验。“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呵’,便是贬义词,是让你警惕。”
留学的日子,生活上较为优裕,“公费留学属于中法文化交流项目,在法费用由法国外交部按月支付。大学城的宿舍一人一间,约30平方米,包括小小卫生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每层楼设公共淋浴室及煤气灶,可煮咖啡烤牛排。每晨有老年妇女服务员来打扫……”但内心的痛苦和压抑只有苦难中国的学生们自己知道——
几十名中国留学生搭乘美国邮轮“海眼”号前往欧洲大陆,船上服务生拒绝收取住在廉价的四等舱里的中国人的小费;
巴黎卢浮宫的一位管理员曾在维纳斯雕像前挖苦地问:“在你们国家没有这些珍宝吧?”吴冠中立刻回答:“维纳斯可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掠走的。你没有到过中国,你去吉美博物馆看看被强盗抢来的中国珍宝吧。”
最受刺痛的经历发生在暑假去伦敦参观,红色的双层巴士上,一位绅士打扮的乘客,拒不接受从中国人手中交给售票员的硬币——作为找零。这“一件小事,却像一把尖刀刺入心脏,永远拔不出来”。
如果说吴冠中“童年认知的苦是穷”,那么他青年认知的苦是歧视,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被人歧视。
“我曾千方百计为学法语而怀抱喜悦,而今付出的是羞耻的实践。但咬紧牙关,课余每晚仍去夜校补习口语。”——为的是学到知识报效祖国。
怎一个“情”字了得
人的情感向背,不光凸显其心灵气质,也常常能够决定其人生走向。对于艺术家来说,情感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理性思维,并早已超越人伦的范畴,而直接反映其艺术天分的高低,也影响其艺术作品的优劣。文章不是无情物,情之伪者不可染翰操觚,丹青亦然。天下绝妙艺术皆出自至情至性之人。
吴冠中91岁人生的千万件画幅、百万字文章、五洲四海的画展与画藏捐赠……怎一个“情”字了得。
巴黎艺术深造深得导师苏费尔皮教授的赏识,一心想为其签署延长公费的申请表。这是多少留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事,但是,经过再三考虑,最终吴冠中还是婉谢了教授的美意。他执意要回到故乡,回到祖国,回到那片饱经磨难的土地与同胞们在一起。
1950年的暑期,吴冠中从巴黎返回,奔向他向往的新中国。行前,他曾给母校——杭州艺专的吴大羽老师寄函一封,倾诉其思念故土的衷肠,赤子情浓,跃然纸上:
“我试验着更深度的沉默,但是国内紊乱接着紊乱,使我日益关怀着你们的行止和安危。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拜之心念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诚如我师所说:茶酒咖啡尝腻了,便继之以臭水毒药。何况茶酒咖啡尚非祖国人民当前之渴求。如果绘画再只是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倍地被人轻视!因为园里的一株绿树,盆里的一朵鲜花,也能给以同样的效果,它有什么伟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许人力物力?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真真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道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简快易喻?”
在谈到回国从事艺术创作的抱负时,他说:“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漠不相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个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情况更糟,我仍愿意回来。火坑大家一起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情系祖国,还是情“戏”祖国,实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难道没有所谓的画家、艺术家在张口闭口爱国爱民族如何如何,可生平作为却难以服众。如果不是十年“文革”被抄走的这封信函又物归原主的话,我们恐怕就再难看到60年前,一位身居海外、而立之年的青年对祖国的这番深情表白。
对于自己的祖国,吴冠中是肝胆相照的赤子;对于绘画艺术,吴冠中则是倾心奉献的恋人。
2005年,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吴冠中艺术回顾展》的自序,以“一个情字了得”为题,追忆了他痴情艺术的经过:
“年轻的我,抛弃浙江大学的工程学习,宁愿降班,转入了杭州艺专。从家庭的贫穷着眼,从我学习成绩的优异着眼,从谋生就业的严峻着眼,所有的亲友都竭力反对我这荒诞之举。我当然也顾虑自己的前程,但不幸而着魔,是神,是妖,她从此控制了我的生命,直至耄耋之年的今天……恋情无边,发现真实与创造美,永远是诱惑科学家和艺术家忘我的动力。别人称颂他们的使命感,这使命感其实是感情的喷发或爆炸……”
作为艺术家兼艺术教育家(常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的吴冠中,告诫他的弟子,名家不等于杰出者,名画未必是杰出之作。伪造了大量的废物欺世,后人统统以垃圾处理。对名家名画应作如是观:要害问题是情之真伪与情之素质,而对技法的精致与怪异不必动心。“情之素质”,是吴先生创造的词汇,那是指所有以艺术创造为生或以艺术鉴赏为业及以艺术爱好为乐者所必备的一种素质,需要悉心涵养。他说:“艺术的失落同步于情感的失落,我不相信感情的终于消亡。情之传递是艺术的本质,一个情字了得。”
吴先生除了大量奇崛画作外,还留下很多珍贵文字,洋洋洒洒有170万字之多,如《我负丹青》(自传)、《我读石涛画语录》、《画外文思》、《艺海沉浮》、《吴冠中文集》(5卷)、《吴冠中文丛》(7卷)等等。这源自他青少年时代的文学情结,渴望追随鲁迅,用文章做文化启蒙,影响世道人心。“越到晚年我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绘画毕竟是用眼睛看的,具有平面局限性,许多感情都无法表现出来,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在我看来,100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有多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其油画《野草》(中国美术馆收藏)表达了他仰慕先贤的心绪,“我从鲁迅的小说中,感受到故乡美。”
说到故乡——烟雨江南的美,必得看吴冠中的画作《鲁迅故乡》(油画1978年)、《江南人家》(油画1980年)、《静巷》(油画1981年)、《双燕》(墨彩1981年)、《水乡周庄》(墨彩1986年)、《忆江南》(油画1996年;墨彩1996年)、《江南居》(墨彩2000年)、《白墙与白墙》(油画2002年)……从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20多年间画家魂牵梦萦的故土,通过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油画与墨彩的交替与叠加,在画面中呈现出一个个基于印象的新奇世界——艺术的境界,如同高飞的风筝系着母亲大地翱翔……“风筝不断线”是他的一个艺术观点,作品是风筝,线是灵感的母体——大众情意。
他说:“这情,万万断不得。”
晚年的吴冠中,一直蜗居于北京方庄小区的最普通的单元楼里,书房仅5平方米,然而,他的画作拍卖总额却高达十七八亿元,仅一幅《长江万里图》(油画长卷1974年)便拍出5000多万元的天价。其拍卖所得或捐赠清华大学作为“吴冠中艺术与科学奖励基金”,或捐赠给其它助学基金会或灾区……明月无私照,艺术不私藏。“我满意的作品约有两百幅,舍不得卖。这些作品都是我的好姑娘,总不能一辈子守着我,总有一天要让她们嫁到好人家。好人家就是博物馆和美术馆。”他捐赠给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香港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等作品400多件。老画家占有着世间最小的居住空间,却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和艺术精神传递给无限的时空,并珍藏于千万人的心灵……
怎一个“负”字了得
关于吴冠中,流传得最广的一句话,在艺术圈内便是“笔墨等于零”,而在艺术圈外的社会上该是“我负丹青”。
这两天,跑了好几家书店,都告之“卖完了”或“昨天还有两本,刚卖完”。书店坐在电脑前负责查询的服务员看我急得一头汗,便解释说:“我知道《我负丹青》这本书,前几年就很热销,就是辜负的‘负’,对吧?不会查错的。”
文学家谁会说“我负文字”,那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画家谁愿说“我负丹青”,这画还怎么卖呀?可吴冠中先生说了,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细细品味画家的一生,“负”字可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辜负”,另一个是“背负”。前者,体现出画家视艺术为神圣,境界之高远穷其一生也难以抵达;后者,则表示画家愿为艺术献身,甘愿做创造之苦工,如同背负重物前行,无怨无悔。
吴冠中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他的一生致力于东西方绘画艺术的“打通”,并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努力探索、尝试,立足本土,留洋取经,古慕石涛,西崇梵高,始终以艺术创新为天职,不畏世人的讥讽、侧目,在技法和形式上了无禁忌,在内涵和意境上殚精竭虑,其作品具有超前意味,可做跨国界的交流而无碍,足为后世楷模。应该说,他用油彩和墨彩为世界谱写了中西合璧的不朽乐章。从此,油画家的作品中有了结合得更加自然的气韵生动的中国诗意,而国画中也有了欧洲现代派、印象派的光影。《大漠》为证,《交河故城》为证,《高粱与棉花》为证……他创造出一种属于绘画的“世界语”。我相信,未来的岁月将会证明这“世界语”的魅力。
事实上,这魅力已显。
高傲的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不仅收藏了吴冠中的《小鸟天堂》(墨彩1989年),并于1992年3月专为这位中国画家破例,首次打破200多年来只展出古代珍贵文物而不展览在世画家作品的规矩,举办了轰动雾都的《吴冠中——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画展。英国王室成员和各界名流参加开幕典礼,《国际先锋论坛报》艺术主编、欧洲权威美术评论家梅利可恩赞誉展主:“发现一位大师,其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开通往世界最古老的大道。这是一项不平凡的工作……凝视着吴冠中一幅从未在欧洲展出过的画作,人们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是近数十年来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发现。”《伦敦经济时报》评论员认为:“尽管吴冠中扎根于中国古老文化之中,其个人魅力属东方,然而,其艺术实践及作品却非常现代……”
欧洲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向中国画家献殷勤,那是他们真正认识到吴冠中绘画艺术的世界级水平和永恒价值。
英国人为其办画展,法国人也不甘落后,1993年,巴黎市立塞纽齐博物馆举办了《走向世界——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巴黎市政府授予其金色勋章。2002年,吴冠中被授予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头衔,他是首次获此荣誉的中国籍艺术家,也是亚洲首位。
吴冠中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是前人的脚印,今天走向哪里,需要探索创新。”他在“油画民族化”、“国画现代化”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中走在时代的前列。而除了多年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硕果累累,他还有许多艺术批评的著述发聋振聩,引发争议。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98年发表的千字文章《笔墨等于零》。
“笔墨等于零”绝不是否定国画画法,而是痛斥那些一味以笔墨为绳墨的匠人习气和泥古不化的遗老作风。那样的话,将会让本来就已经式微的国画艺术走上绝路。“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我国传统绘画大都用笔、墨绘在纸或绢上,笔与墨是表现手法中的主体,因之评画必然涉及笔墨,逐渐,舍本逐末,人们往往孤立地评论笔墨。喧宾夺主,笔墨倒反成了作品优劣的标准……但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吴先生的这一观点,脱胎于清代画家——“苦瓜和尚”石涛的画论《画语录》。
石涛,很早——早在国立杭州艺专时就是吴先生的心仪。
“中国现代艺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西方推崇塞尚为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贡献属于发现了视觉领域中的构成规律。而石涛明悟了艺术诞生于‘感受’。”吴先生对石涛诸如“古之须眉,不能长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知有古而不知有我。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言论颇有相见恨晚之叹。其“笔墨等于零”的断喝,也是代石涛在现代发表锐见。有人说,“零”之说有雷霆万钧之力,可以重振国画的旗鼓。
当然,吴先生的艺术观点还有“形式美”和“抽象美”的呼吁,以及对美术协会和机构的微词等,皆以赤诚之心吐谔谔之言,其情可感,其志可嘉,也是有所“背负”者的有所担当。
冬天可读吴冠中的文字,读之血热;夏天正可看吴冠中的画作,观之凉爽;而春秋可睹吴冠中的为人,如春风拂面,秋月临窗,温暖而澄明。
吴冠中先生不仅无负丹青,亦无负苍生。
-
湘炎灵韵——陈越胜炎..
九月十日上午十时,中华世纪坛一楼中心展..
-
广州艺博会2011夏季艺..
2010年,随着国内经济的迅猛增长、国家对房产的调..